The Influence of Expat Teachers
在NYU Shanghai已经一年有余。这段时间当中,上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课,也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教授。
一个沉迷学习的sophomore的自白在NYU Shanghai已经一年有余。这段时间当中,上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课,也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教授。对于我这么一个在传统中国式教育中奋斗了十余年的“职业学生”来说,进入这样纯粹的西洋式的环境是一次极大的转变。就如当年留美的晚清孩子们一样,我也剪去了自己头上的那根小辫子,换上了一套得体的西装了。于我而言,那些来到中国的二十一世纪的利玛窦们,在对于“学习”和对于“老师”这两个词的诠释上给我带来了尤其深的影响。
学以致用高考大概是这辈子目前为止走过的最长的套路,以至于为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不知疲倦的奋斗了十几年。中国式的教学思路大抵也是契合这样的套路的:老师上课教会你1+1=2,作业做2+2=4,高考考1+2+4+8+16+…在这里教授们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如果上课教会了你1+1=2,你要去探究2+2是不是等于四,并且找出为什么。这两个例子的区别就在于对于“用”的理解不同。原先我所接受到的“用”,不过是举一隅以三隅反,其核心在于了解。可是对于上纽的教授而言,无论是课上作业还是课下交流,单单停留在了解是完全不够的。就以中国学生必须要上的EAP课程为例,你可能在作业上只需要听两段关于sharing economy的演讲。可是到了课上你需要做的不是告诉professor你听到了什么,而是讨论共享经济在中国是否可操作,可能会遇到怎样的阻碍。你一个学期获得了关于sharing economy的基本理论,你需要自己建立一个模型来测试是否能够实际运营。简要的来说,我在这里所认识到的“用”,不只停留在“了解”,而更是一种“探索”。陈兼教授曾经告诉我:“如果你读一本书只停留在了解的基础上,那就不会有现在的新冷战史研究了。”其理大抵如此。
亦师亦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里一直带着尊重师长这么一条,只是往往这样一条规矩会被我们自己过分解读,以至于对老师的感情变成了纯粹的畏惧,与老师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有着明显上下级的区分。但是在这里,教授们更希望我们把他们视作朋友,而不是简单的师生:我可以发一封邮件和教授约战乒乓,然后被老头子用一柄比86年的拉菲还要老古董的乒乓球拍打得满地找牙;也可以愉快地谈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赚钱的大计划;我甚至可以就教授上课所讲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然后在隔壁的星爸爸里点上一杯咖啡撕上一个下午的逼。Non是最开始这样影响我的老师。一脸不羁的胡子,随性写意甚至略显风骚的上课风格,以及与我们相差不多的年龄。他会给我发一些自己的所思所想,有时是个搞笑的段子。我也和他聊上海,听着他用蹩脚的上海话引着我去很多我原先不知名的地方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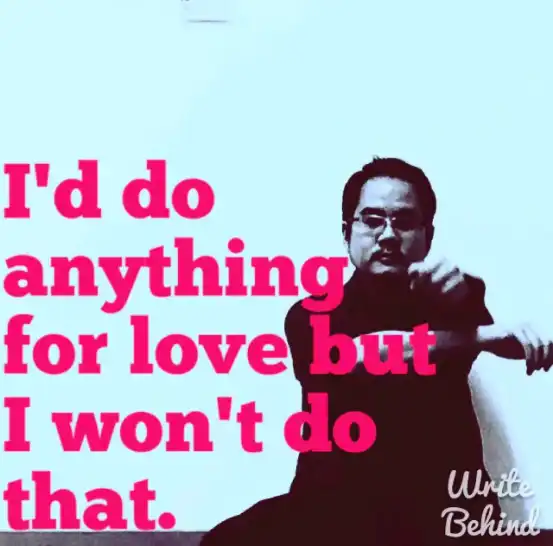
在逐渐内化这样的影响之后,我也愈发觉得这样的师道接近于孔子所提倡的以贤于己者为师的理念。在这里学生和教授平等开放的交流,不需要带有任何的顾忌。无论邮件还是聊天,教授们的口头禅都会是“Alwaysssss for u”。当我敲下这许多行文字的时候,忽然想起下午又将在café约教授见面,谈谈我对于时下网络评论的观察和对于爱国的浅见,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research和之后的paper做准备。那么,上路吧。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Ray Lin.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managing@oncenturyavenue.com to get in touch. Photo Credit: Ray Lin